安化黄精主题文学创作征文大赛一等奖
又是黄精结实时
作者:邓 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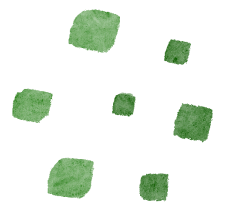

谨以此文
致祭渐去渐远的梅山药人药俗。
——题记

天朗气清,白云悠悠。仿佛有只巨手拽着轻纱在空中拂拭过,天瓦蓝瓦蓝,连绵的山岭虽不似夏天青翠,却绿得蓊郁、深沉、干净,这是一个离霜期还远的秋日。父亲的心情特别好,他收回看天看山的目光,征求意见似的对我说:“我们去荒尖崖挖老虫姜?上半年我答应过你福叔挖几副药的。看我能不能爬,若是爬不上,我们就在后山挖些算喽。”“您有这意思爬不上我爬嘛。”我说。

是的,春天里,邻村福叔来看望父亲,无意中说起自己这些年全身无力、疲劳、时有咳血的情况,感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当时父亲说,六十多岁人身体还不至于滑坡这么快,问了他的症状后父亲很有把握地说,哪天给扯几把草吃了就好。福叔走后又有叔伯来陪父亲打讲嘲白,其时我还问起过为什么挖药叫“扯草”,母亲说,扯草就是扯草药,土生土长这都不懂简直笑话,我当然知道是扯草药或挖草药,我在家呆的时间并不长,真不知道为何这么说。大家纷纷讲起各自的见解,家乡离医院远,有病看医生不方便,也耽误工,小病多是就地诊治,村里上年纪的人都能认识上百种草药,会治几种病。这叫法有两重意思:一是给人治病是行善,诊好了,不需要记得也不要感谢,乡里遍地药草,扯把草于村人是举手之劳;另外,也是行医者对疾病的蔑视,什么病都不要咋咋呼呼,吾乡吾土我一把草就对付得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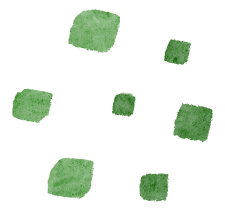

那段时间连续阴雨,父亲感冒并发了心肺积液的老毛病,给福叔扯草的事也就被耽搁了。后来住了两次医院,这
一次前天才回,邻里多还不知道,父亲有些闲静。见他有兴致上山我应了声“好”便背起背篓,荷了锄头,父亲从刀具匣里拿了把小柴刀,将一个折叠齐整的布袋放进我背篓,我们就出门了。凉风嗖嗖,一对长尾鸟从头顶飞过,在对面山上的树梢停下来,互相嬉戏打闹,一会又飞回来,好像炫耀那黑白相间的羽毛和灵巧的身姿。父亲确实好多了,但是爬山还是气喘。他说他只能慢些爬,能不能爬上荒尖崖也还不晓得,我们一边走,一边将看到的药采挖下来,我说时间早不急,问他一定要去荒尖崖采老虫姜?他说老虫姜被称为仙人余粮是好药,荒尖崖人们轻易不去药草生长时间长,药效更好。荒尖崖在屋后右边两山相汇的地方,从对面山上望,好像两座山想靠拢,却被一块硕大的岩壁硬生生撑开,这岩壁就是荒尖崖。荒尖崖陡峭险峻,岩壁中镶嵌着星星点点的小石子说是冰碛岩,小时候我们常去那逮白鹭,因为崖的两边是深涧,崖上水气重,常年云雾蒸腾,崖上植被丰茂,遍
地药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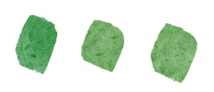
我们一路采着药,采了半篓,父亲说,药量已经足够多了,我们歇歇停停地走,讲点草药的“下数”,他先讲的是药的名称。说草药多有学名、药用名和俗名,不做药时称学名或俗名,一听就懂;作药用时一般称药用名,只行医挖药的人懂,比如天花粉、叶里藏珠就是瓜篓和铁苋菜的药名。叫别名有的是为了避讳,我们这里什么都是药,但脏东西叫出名字就恶心了,比如人粪猪屎叫本名谁还敢吃?配成药就叫人中黄、猪苓;有的是要用它的威名镇住邪气或病毒,比如盐肤木叫飞蜈蚣,灶心土叫伏龙肝,黄精叫老虫姜……他说这称谓是不是为了保持一份神秘感他也搞不清,也可能是一些人觉得身边的东西太普通怀疑药用效果医者有意说得玄奥,响亮的名字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心理暗示。至于杠板归称蛇不过,落地生根称打不死明显是安慰人它的药效不容怀疑。我有些惊异他的理性与时尚,故意说是迷信,他不认同。他又说到哪采药采什么药都不能把某种药采尽,得留种。我说医院里的药是到市场收购的,药农采药时可不按他说的规矩,人家能赚钱哪管它被挖尽,先变钱了再说。他有些生气,说我读书变坏了,别人不会这样做,至少他知道的安化人挖药都不会这么挖。其间我说医院开方用的应是学名也能治好病,他说,你不常听人说草药郎中治病比医院好的
快吗。我发现他因为久病脾气变得火爆,不怎么耐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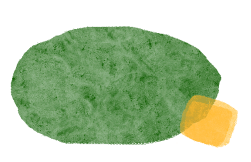

他的“下数”灌输得不是很愉快,但我们依然这么地聊,聊着聊着,转过一个弯就到了崖下边,路越发陡,看父亲累了,我让他就地休息,他遗憾不能上崖,把布袋递给我,叮嘱我按他讲的“下数”选苗壮硕的黄精挖七蔸。强调要和之前采药一样朝前走挖,不挖回头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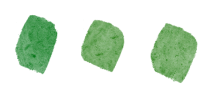
崖壁上好多地方没有土,更没有路,须借助旁边的藤蔓和树枝才能上。崖上乔木灌木之间都很通透,草丛象顺着山坡梳理过一样,崖上微微的凉,有风拂过,挟来阵阵花草的香气,沁人心脾。到得高处打一望,嗬,黄精还真不少,这季节树木都是苍绿的,黄精叶翠翠地绿着,不枝不蔓非常独立,一枝枝宛如架架小排梯,宽皮大叶顺着茎向两旁伸出,串串果实谦谦下垂有如学位帽上的流苏,这是黄精之佳品多花黄精,我在一株杆茎拇指粗的黄精旁蹲下来,顺着“流苏”往下捋心想这籽实应该可以做种了,其时我的神情一定俨像导师或大学校长给心爱的学子拨穗。视线内大的有十多蔸,我朝父亲喊,是不是多挖点。他说大就少挖点,挖五蔸吧,离苗 把远下锄。我在离苗约20公分的地方开挖,可还是挖烂了,拼到一块有脚盆大,第二蔸第三蔸都差不多大小,第五蔸朝一侧长着,挖出来摆到地上比腰带还长。我把四蔸放篓里背着,长的双手护在胸前,到得父亲身边,他伸出两臂比划了下说有一庹长哩,他告诉我怎么识别黄精的年龄:它的根块是一个个节砣组成的,一个节砣就是一年,数一下这黄精长了十七年。我感叹挖起来喜人真舍不得停手,父亲严肃地说他刚讲了“留种”的事,说“好吃婆娘”也留种,“叫化子”也留种。接着他说起一个乞丐讨人黄瓜宁愿挨饿将种退回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格局。

蝉声嘶哑,流水淙淙。路边一口山塘冒着凉气,父亲说就在这洗药,要我梳理下头发,将身上粘着的草屑抖掉。又示范性地掬水漱口、洗脸、洗手,他把药倒出来要我面朝水源洗药,说给人挖药就得聚一片心,想着好向着好。我洗药的时候他讲为什么不挖回头药,不朝水流方向洗,寓意是病不回头,不反复,一路滔滔好熨贴。他说,药要洗干净,干干净净人家才敢吃,他讲起多年前的一个教训。邻县桃源妇女结婚多年没怀上孩子,由婆婆带来请他挖药,诊断后父亲给她挖了五付,说服了下个月就会有反应的,可一个月两个月就是没动静,父亲觉得奇怪,他治妇科病和不孕不育症远近有名,挖的“喜药”多是服后见喜,这次居然就无效,怀疑她们没按法吃或者做了其他处理,媳妇支吾着说她看有药没洗干净自己重新洗过。父亲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的药除了药草的效力外,还挽手诀画了符,有师傅的元神在里边,是不能再洗的,父亲为耽误了她的时间自责多日。


吃罢午饭给福叔配药,父亲说师父传授挖药是挖单数,三付、五付、七付……药方里的药种数是单数,总药量也是单数,九株、十五株、二十一株……每付药苗茎要理整齐,根须要捋抻敨,药配好了,父亲拿过来并到一起,眯着眼睛对着药念念有词,声音很轻。福叔是之前的肺病没完全好,脾胃虚亏,方中黄精为主要药,用得多。因为根块大,配药不按蔸而是按块计,还剩不少,父亲说,趁天气好,我们把它九蒸九制。我问他这么看重黄精,为什么不用于自己的身体调理?为什么平时不弄来家里人吃?酒店还有黄精做成的菜肴啦,他说大自然赐给人类是做药用的,不然,人们早就会种在园里田里。做菜吃是那些人的事,天天吃肉的感觉都没隔些日子吃肉的好。过年回家见到福叔,他气色不错,说他的病已经好圆功,岩山都可以蹬崩了,搭帮我父亲。秋天里一个蝉声如咽的日子,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九蒸九制的黄精他没有认真享用过。
又是黄精结实的季节,我想起父亲。

---END---

